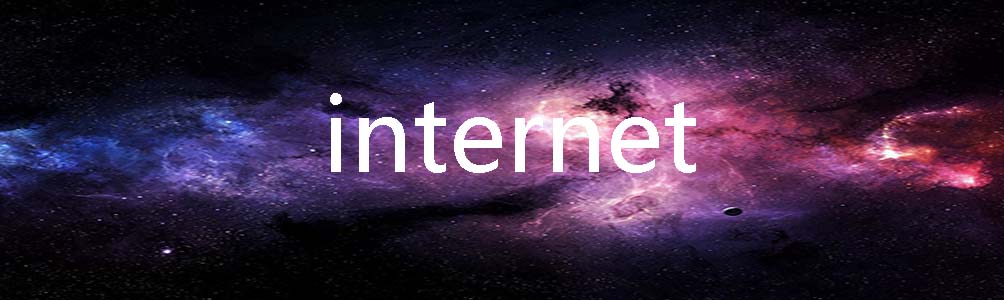陳偉武
選堂饒宗頤先生是當代著名史學家?經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文學家和書畫家。其學術研究規模恢弘,成就多方,涉及人文科學的許多領域。其著作有學者分爲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和書畫等八大門類。每個門類都有重要建樹,今擇其涉及語言文字學者略作紹介。
饒先生在甲骨學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劉釗先生曾有專門評介。[1]而《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則是饒先生的代表作,出版於年,開創以“分人研究法”爲綱?全面整理甲骨卜辭的新體例。此書例言指出:“治卜辭者,無不盛言分期,因有所謂‘斷代’及‘分派’二種方法,……鄙見無論‘斷代’?‘分派’,必先以分人研究爲基礎,本書之作,即在提岀卜辭之分人研究法,使有卜人記名之刻辭,得一綜合之整理。”全書二十卷,八十多萬字。卷一“前論”,卷二“貞卜人物記名辭式釋例”,卷三至卷十七“貞卜人物事輯”,搜羅當時能見到的所有與“貞人”相關的甲骨資料,在每個“貞人”之下再細分“卜雨”?“卜晴”?“卜風”?“卜雲氣”?“卜月食”?“卜水”?“卜夕”?“卜旬”?“卜年”?“卜狩”?“卜往來”?“卜夢”?“卜疾病”?“卜祭祀”?“卜邑”?“卜征伐與方國”?“卜所見人物”?“雜卜”?“成語”等項,逐項羅列原始材料,隨文詮釋疏證,對關鍵問題則詳細考辯。卷十八“備考”,卷十九“結語”,卷二十“附錄”,附有“貞卜人物同版關係表”?“各期貞卜事類表”?“祭名索引”?“成語索引”?“地名索引”?“人名官名索引”等,極有參考價值。
饒先生主編《甲骨文通檢》,具體編纂由沈建華女士負責,共出版五巨冊,每冊有饒先生長篇前言,闡述與各分冊相關的甲骨學問題,如第一冊前論貞人問題與坑位。第一冊“先公先王·先妣·貞人”,第二冊“地名”,第三冊“天文氣象”,第四冊“職官人物”,第五冊“田獵”。這一大型的甲骨文分類資料索引,爲人們更多更好地使用甲骨材料?推動甲骨學的深入發展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饒先生利用長期在世界各地從事學術活動之便,不辭辛勞,搜求散失海外的甲骨資料,並加以整理刊佈。有多種著作行世:《日本所見甲骨錄》?《巴黎所見甲骨錄》?《海外甲骨錄遺》?《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等。
饒先生《“玄鳥”補考》一文,指岀殷代文獻出現“玄鳥”二字的合文,以近年刊佈的安陽花園莊東地遺址出土的兩組龜甲卜辭爲證,“這組辭是占卜子而其人的疾病,而向玄鳥祈禱,玄鳥一名,作二字合文……使用合文,正因爲玄鳥是殷代的主要神明,作爲特例。”從而說明殷人久已流行“玄鳥”崇拜的神話。
戰國文字研究也是饒先生長期耕耘且成就卓著的領域。年,長沙子彈庫楚帛書被盜掘岀土,後來流失美國。饒先生對楚帛書的研究,數十年一直未曾停息,先後發表論文和著作多種。年,帛書收藏者沙可樂將放大十二倍帛書紅外綫照片張郵贈饒先生,饒氏根據這套照片製作了新的摹本,其精確度最高,與此前最有代表性的商(承祚)氏本和林(巳奈夫)氏本相比,可正確無誤辨認的字竟激增了一百數十字,至此,知帛書實存字數可達文。由於饒先生爲學術界提供了準確可靠的原始材料,並且新認岀了百餘帛文,楚帛書的研究產生了新的飛躍。李學勤先生曾指岀帛書邊文與《爾雅·釋天》中的月名有關,惜其所據摹本邊文殘泐過甚,不易理解,故其觀點未獲認同。年饒先生在紐約對帛書原物作了仔細辨認和反復勘讀,撰《楚繒書與爾雅十二月名核論》,證成李說,從此,帛書邊文十二月名始被正式肯定下來,“始取(陬)終(塗)”的十二月序亦隨之獲得承認。由於帛書月名與其結構及性質密切相關,饒先生一貫主張以八行正置而十三行逆置的置圖方式,闡釋其因由說:“甲篇(八行)道其常而乙篇(十三行)言其變,故甲篇居前而乙篇列後,前者順寫而後者倒書,所以昭其順逆。兩篇特殊結構的用意,可以推知。”此說揭示了楚帛書中間二篇顛倒爲文的奧秘,是迄今最爲合理的解釋。以八行爲正的置圖方式也得到進一步的確認。《楚帛書新證》是饒先生三十多年研究經驗和心得的結晶,在釋讀甲乙兩篇帛文及某些疑難問題的探討上,創獲甚多。如據《易緯·乾鑿度》知庖犧亦號大熊氏,與帛書篇首“曰故(古)大熊雹戲”一語正合;據《墨子·非攻》知楚先世居於睢山,可證帛文“居於”乃楚先所居之地,而“”亦可定爲“睢”之繁文;據《地母經》知女媧亦曰女皇,則帛文“某某子之子曰女皇”確指女媧,而由帛文雹戲?女皇?四神?炎帝?祝融?共工等所組成的神話系統具有鮮明的南方色彩,均與楚之先世有關。帛書篇首殘缺最甚的一段文字因此得以貫通。
除楚帛書外,饒先生對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雲夢睡虎地秦簡?長沙馬王堆帛書等楚地出土文獻都深有研究,建樹良多,曾憲通師已經作過精詳評述。[2]例如,對曾侯乙墓鐘磬銘辭若干待定的古字作了辨認,結合傳世典籍中的樂律資料,對樂律術語?五聲倍律的異名以及一些樂律史上的問題試作說解,考知鐘磬銘辭記載周?曾?楚?齊?晉各地不同的律名,而楚國使用的律名,則以呂鐘爲黃鐘,六律中有四個稱曰某鐘,且特別指明其濁音,並不沿用周律,自成體系,此爲前所未知。與曾侯乙編鐘同出的漆箱蓋,上有朱書文字六行20字,饒先生應湖北省博物館之邀,最先作了釋文,不僅破譯了這些古文奇字,還進而探討了古代樂理與天文的關係,使漆書的天文學內容與同岀樂器群之間的內在聯繫得以充分的揭示。朱書最末兩句,饒先生原釋爲:“所尚若敕,經天常和。”年,青年學者劉國勝以包山簡爲證,改釋末句爲“琴瑟常和”。[3]饒先生從善如流,援據劉說,更從新岀郭店簡和傳世音樂史料續作推闡,令漆箱蓋朱書文字釋讀益加可信。[4]日書是古代日者占候時日宜忌?預測吉凶的曆書,年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有兩個寫本,共有竹簡枚?字,這批材料出土後,一度受到冷落,饒宗頤和曾憲通兩位先生合著的《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是第一部研究秦簡日書的專著,通過“建除家言”?“稷辰”?“玄戈?招搖”?“反枳”?“歸行”?“禹符?禹步?禹須臾”等十二個專題,結合傳世典籍,詳加疏釋。如勘《淮南子》“剽”與“杓”異文,證“反枳”即“反支”之殊寫。林劍鳴先生嘗稱此書爲研究秦漢數術的“奠基之作”。[5]
饒先生對馬王堆帛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帛書《易經》?《老子》?《刑德》及醫書上,如論文《帛書繫辭傳“大恒”說》指出,《周易·繫辭》通行本“易有太極”句,帛書本作“易有大恒”,“極”之作“恒”,當是漢以前《繫辭傳》的本來面目。而“大恒”轉寫爲“太極”或“太一”,則是異名同實。“太一”在楚爲主帥,而“恒”的道理在楚人著述中亦甚流行。再如帛書《刑德》中四仲之神有“湍王”?“攝氏”,饒宗頤認爲“湍王”即顓頊,與炎帝相對之神,非顓頊莫屬;“攝氏”即攝是,當即攝提,絕無疑問。顓頊?攝提之名,過去未見於出土文獻,首見於帛書,彌足重視。“攝氏”或作“攝提”,既是星名,又是神名,往者或謂“攝提格”爲外來語,此可證其不確。
饒先生是較早研究戰國楚簡的學者之一,年所撰的《戰國楚簡箋證》,董理疏釋仰天湖楚簡,不少發現至今仍爲古文字學界所津津樂道。部分戰國荊門楚簡流失海外,年在臺灣高雄訓詁學學術研討會上,饒先生作了題爲《在開拓中的訓詁學》的專題報告,發表並考釋了《周易·睽卦》六三爻辭的一枚殘簡,引起學術界的熱烈反響。《緇衣零簡》以傳世本《禮記·緇衣》合證,考釋了香港中文大學收藏的一枚楚簡。郭店楚簡發表後,饒先生又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從新資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儒道學派試論》?《從郭店楚簡談古代禮樂》?《詩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簡資料爲中心》等。上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亡志”,饒先生反復申論,指岀“”當釋爲“吝”,而不應讀爲“隱”。《孔子詩論》簡8“《十月》善諀言”,“諀”或讀爲“諞”,或讀爲“譬”。李零先生認爲:“‘諀言’是訾議之言”,於文可通,不必讀爲‘諞言’。”[6]饒先生指出當讀如字,指訾毀,不必假借,證據是服虔《通俗文》:“諀言乃訾毀之語。”《廣雅·釋言》:“諀,訾毀也。”《集韻·五支》:“諀,諀訾,好毀譽也。”饒先生考釋《孔子詩論》簡11“《關雎》之”:“‘’字詩簡共三見,一作‘’,二作‘’。其字從巳甚明顯不是從己。余前讀爲‘巹’,未安,宜另從‘巳’字着手。是簡之中,‘也’與‘巳’二字大有分别……辰巳之‘巳’,久已用爲‘巳然巳止’之‘巳’。此字增攴或又旁,均是後加,可直釋爲‘巳’。以‘巳止’之‘巳’說之。《關雎》之‘巳’,猶言‘《關雎》之止’。”
《詩與古史》一文以上博簡《子羔》所見玄鳥故事的記載同甲骨文等考古資料及傳世文獻相結合,闡述早期殷史中的玄鳥傳說。
《說糢餬?糢糊?模糊》一文爲俗字源考釋之作,以杜甫《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適)》詩的多種刻本異文爲例,結合蘇軾《石鼓歌》及清人仿貞觀法書真跡,論證現代熟語“模糊”原當作“糢糊”,從而對《漢語大詞典》米部的“糢糊”條和木部的“模糊”條作了補正。並將此詞詞源溯至春秋,以爲莒國人名“‘瞀胡’當是‘糢糊’的記音,古有是語,現在無人知道了。”“模糊’應該是‘糢糊’的借音,原有當作糢,完全沒有錯誤,不應妄指‘糢’爲非。杜詩被刻成模糊,即其例證。糢餬?糢糊?模糊,多少年來,人們都在糢糢糊糊之中……因草此文,予以澄清。”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全書分上下篇,共十節,約16萬字,是饒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此書多方追溯漢字演化的軌跡,並與腓尼基字母?蘇美爾綫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較,從全新角度探討漢字起源問題。饒先生指出中國歷來的“書同文”政策造成語?文分離,文字不隨語而變化,而且漢字結合書畫藝術及文學上的形文?形聲的高度美,終使漢字這一參天大樹卓然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文字?文學?書法藝術的連鎖關係構成了漢文化的最大特色。此書還揭示了漢字未形成初期陶器上的大量綫形符號,反映了古代閃族人使用字母並嘗試采擇陶符以代替借用契形文的雛形字母之特殊現象,從而提出了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學假說”。最後指出,不使用字母是中國古代就作出的明智抉擇。
中西語言文字及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饒先生取得重要成就的方面。饒先生從小愛讀佛書,諳熟佛典,後來對梵學有精深旳研究,對漢語音韻學也有深邃的修養,詳參李新魁先生的考述。[7]《梵學集》共收論文27篇,論述梵學與音韻學者凡11篇。在這11篇論文中,分別討論了漢語四聲的起源問題?鳩摩羅什《通韻》所闡述的悉曇章以及悉曇章在我國傳播的時代和過程?梵文十四音的內涵及各種異說?梵文四流母音“魯流盧樓”的傳譯?取捨及在後代的應用與流變?佛咒用字“吽”的考釋?六朝聲律學所受梵學的影響等等。
早在漢代梵學傳入並產生廣泛影響之前,我國文人由於語音知識的積漸感悟而創造了反切。但是,齊梁時代岀現了屬於反切輾轉運用的?反語?,則明顯地受到梵學拼音知識的影響和推動。沈約有紐字之圖,撰《四聲譜》,饒先生認爲當與周顒所作“體語”有淵源關係:“以紐切字,實倡自周顒。顒好爲體語。體語者,即梵語子音之體文。……體文取義殆本諸南印度字母。周顒既善體語(文),是深明梵音紐字,故能以切字爲紐以論四聲,爲沈約之前導。約進而造《四聲譜》,取以制韻,定其從違,示人以利病,遂成獨得之秘。”並指出:“余謂沈譜之反音,乃從悉曇悟得。”“周顒之體文合四聲,可謂華梵比較語音學孕育之奇葩。”饒先生的研究,足以揭示漢語音韻學史上韻圖產生之源。
陳寅恪先生曾經認爲漢語“四聲”的產生是由於受了梵學的影響,陳氏在《四聲三問》一文中指岀:“中國何以成立一四聲之說?即何以適定爲四聲,而不定爲五聲或七聲,抑或其他數之聲?”這是因爲“中國文士依據及摹擬當日(南齊永明之世)轉讀佛經之聲,分別定爲平上去之三聲。合入聲共計之,適成四聲。”[8]陳氏之說頗受音韻學者的推崇和引用,俞敏先生提岀過反對意見,饒先生則從理論和歷史事實上對陳說作全面而具體的剖析先後發表了《印度波你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四聲說與悉曇之關係兼談王斌?劉善經?沈約有關諸問題》等論文,論證陳氏謂四聲仿自轉讀?創自周顒及沈約之說不可靠。日本學者平田昌司撰文爲陳氏辯解,李新魁先生力證饒說確不可易。悉曇章在我國的傳播,對漢語音韻學的發展有頗大影響,其傳入時間通常認爲在唐代,但饒先生指出,後秦鳩摩羅什所撰的《通韻》,即已包含悉曇章的內容。從而將悉曇章在我國傳播的時間大大提前。
《通韻》中謂梵文“本爲五十二字”,“就裏十四之聲,複有五音和合”。五十二字是指五十二個字母,十四聲是指梵文的十四音,五音是指五類“毗聲”。饒先生一方面分析和總結了“十四音”的諸家異說,概括爲鳩摩羅什?道朗?智藏?寶亮?僧宗?道亮?智秀?僧旻八家的不同說法;另一方面,論述“梵文四流母音???????與其對中國文學之影響”,認爲“唐代《悉曇章》中以‘魯流蘆樓’四字爲和聲,到了後世,遂超很複雜的變化”。其用作和聲的技巧,已由鳩摩羅什傳到了現代。饒先生進而考定這四流音在我國各種典籍中的譯法以及它們存廢的情形,指出:“???????四個字母,除r母音外,已有許多世紀未用。現代字母並無此四字。中國尚存這四個字母,用途又截然不同,真是奇妙。”由於悉曇章的傳入,促成了漢語字母的產生,並導致了漢語等韻圖的岀現,使音韻學在其內容上圍繞等韻圖及其製作?拼讀原理而創造的“等韻門法”等的產生,從而形成了“漢語等韻學”。饒先生指出:“從悉曇音理可聯想到種種門法,後來之等韻學,亦由悉曇孳乳而來。”
佛教咒語有多種多樣,但誦佛真言常用者有“南無阿彌陀佛”和文殊菩薩的“六字真言”,即“闇婆髻馱那麽”,又稱爲“陀羅尼咒”。佛家謂誦此咒可“滅一切罪,生一切善”。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論及“吽”字應作“”,謂“蓋藏語音如是,中土傳寫訛誤,昔亦未知,後習藏語,始得此字之正確形讀”。饒先生撰有《吽字說》,專門駁正陳氏之說,認爲此字雖小,但“這個問題在宗教史上關係相當重大”,不可不辯。饒氏指出,字甚晩岀,初見於《集韻》,讀爲匹降切,與“吽”(hum)之音無關;吽字見於殷代;吽即吼字,《玉篇》音爲呼垢切,義爲“牛鳴”,與??呴等實爲同一字;日本空海(約當唐代)寫有《吽字義》一文,吽字有四義:賀字義?阿字義?汙字義?麼字義,“全譯此吽以四字成一字。”空海之說,“自是唐時密宗金剛界大法”;元人以敘利亞文hm譯爲吽;咒語中吽又寫作??;漢文都以hm或hum對譯爲吽,或作??,在文獻上未見有作者。“吽字用於六字大明陀羅尼,自北宋以來,已極流行。”
饒先生不盲目崇信前輩學者的論斷,在梵學與漢語音韻學相關的許多重要課題上抉發新義,多所建樹。
饒先生被學界稱爲“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博古通今,中西融貫”,既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根柢,又熟諳西方治學門徑;既運用多學科的知識解決語言文字學的難題,又以語言文字學爲工具,拓展其他學科的學術領域,使語文學研究與中外古代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取得了許許多多獨創性的成就。
附記筆者曾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約,爲《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一書組稿,本人負責撰寫的條目有“饒宗頤”?“曾憲通”和“馬宗霍”三條,每條字數五千八千不等。年,該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可惜編輯改變原有體例,悉將篇末“某某某執筆”字樣刪去,心頗慊慊。時隔十餘年,檢出舊稿,補加注釋,増加介紹饒公新發表的相關論著,完成了這篇論文。小文蒙石小力君校閱補字,謹志謝忱。
注釋[1]劉釗:《談饒宗頤教授在甲骨學研究上的貢獻》,《中國圖書評論》年3月號,頁。
[2]曾憲通:《選堂先生與荊楚文化研究》,《華學》第二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肚,年)。
[3]劉國勝:《曾侯乙墓E61號漆箱書文字研究——附瑟考》,《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年),頁-。
[4]饒宗頤:《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談老子門人的琴學》,《中國學術》第一輯,(香港∶商務印書館,年),頁1-11。
[5]林劍鳴:《曲徑通幽處高樓瑿路時——評介當前簡牘日書研究狀況》,《文博》年第3期。
[6]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年),頁36。
[7]李新魁:《梵學的傳入與漢語音韻學的發展》,《華學》(中山大學岀版社,年)第二輯。
[8]陳寅恪:《四聲三問》,《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End
本文選自《饒宗頤學術研究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年。
作者簡介
陳偉武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所長、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山大學中心平台主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兼秘書長、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澳門漢字學會副會長、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執行院長。
▼往期精彩回顧▼NO.18饒學文粹丨曾憲通:選堂先生三重證據法淺析
NO.17饒學文粹丨劉樂賢:饒宗頤與簡帛研究
NO.16饒學文粹丨萬毅:饒宗頤先生的琴學研究與“樂教”論
……
长按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