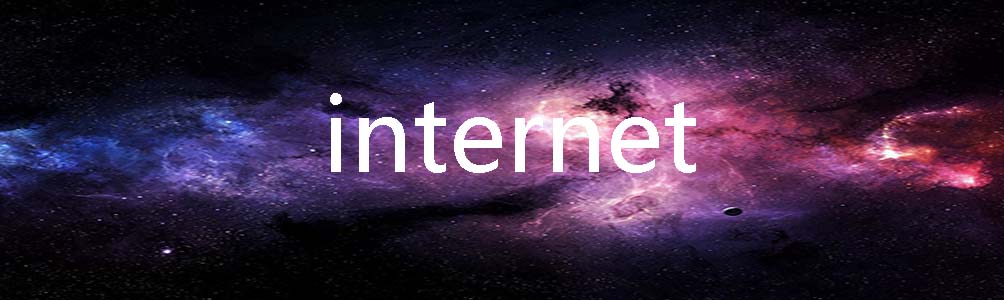(接上)
棺材倒是没买,原因是有一次看病,一位病友告诉母亲,说她的一个什么亲戚,也得了类似的病,就去看中医,结果中医给治好了。
母亲喜出望外,连忙问病友,这位中医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他?
病友说,中医叫江春华,医院就诊,好像一周就出诊一次,而且挂他的号很难。
已经彻底绝望了,却突然又点燃了希望,这希望该是多么值得珍惜啊。于是,母亲第二天起个早,拖着病体,医院,去找江大夫看病。
没有挂上号。
江大夫本就是一周出诊一次,这一天,江大夫不出诊。
无果而归的途中,也有所得,那便是终于打听到了江大夫出诊的具体日子。
再一次起个大早,赶过去。却早早没有了号。
母亲悻悻而归时,却更有了希望,直觉告诉她,这个医生一定行!那么多来求诊的病人不是傻子!
于是,巴巴地等到下周那一天。母亲头一天晚上沐浴更衣,把闹钟开到凌晨三点,匆匆洗漱,也不吃饭,医院。
本以为这一次来,肯定能挂上号,却没有想到,医院的大门。
这么多人挂号,还能看得上病吗?
母亲心下怀疑,想已经来了,就先排上队吧。
三个多小时过去,快要开始挂号了,医院方面就有人出来维护秩序。
一个戴“红袖套”的工作人员,从挂号窗口一路数着人过来,在离母亲很远的地方就喊:你们后面的,不要排了!排了也没有号了。
队伍有点松动,但还没有散开。
“红袖套”提高声调又喊:听见没有?告诉你们不要再排队了。一个专家,一天能看多少个病人?
队伍一点一点扭曲、松散、变形,开始没了模样,最终四散而去。
母亲这时早已体力不支,医院外的冰冷的马路丫子上。
下周必须再来,提前一天来,而且这一次,医院过夜,一定要挂上号!母亲暗下决心。
我如此烦琐地述说母亲挂号的经过,无非是想表达看病之难。
其实,我在述说的时候,也疑窦丛生。
母亲病得那么重,她还能亲自去挂号,而且排队等一个晚上?
如果不是母亲亲自去挂的号,那是谁替她去挂号的呢?
应该不是父亲,因为当时他还在部队里。
所有这一切,我当时听母亲讲述的时候都没有问清楚。
不过这都无所谓。关键是,最后一次,母亲挂上了号,看上了病。
然后,一切都变得毫无悬念。她的支气管扩张,就在服了大约二十天的中药汤剂以后,就一天天转好了。
等到有了我,我从母亲嘴里听到这个故事时,虽然母亲仍然一身都是病,但她的肺,她的气管,我根本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好。如果不是她告诉我这一经历,我哪里知道她还得过这样要死人的病!
这个故事,是我开始神往中医的开始。
接下来的另一个我母亲的故事,令我对中医无比崇拜
这一次是眼疾。
母亲三十多岁有一段时间,她的视力突然开始急剧下降。
下降到什么程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行的人民币纸币,上面的钱数,她都看不清,需要用手根据纸币的大小来判断面值。
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半瞎。
为了治眼病,母亲又一次医院西医眼科再看遍,得到的答复又是两个字:没治!
绝望又一次降临到母亲的身上。
也许是母亲运气好,危难时候总会有人帮助她。
这一次,又是一个病友,在聊天的时候告诉她,可以去看一看中医,一个老中医,叫姚何清,是一个神医,很多疑难杂症,他都能看好。
因为有上一次的经历,母亲得到这个消息,已经黑暗的心灵,一下子光明了起来。
想必挂号肯定也很难,不过母亲最终看上了病。
这是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中医,白胡子有一尺长。看病的时候,只望——看了看母亲的舌象,闻——听母亲讲述病情发生、发展的经过,切——认真地号了一下母亲的脉,然后,几乎没有讲一句话,就用毛笔悬腕写下了药方:天仙藤、五味子……
再然后,母亲就听到女护士在叫:下一位!
等到母亲连忙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收好药方,朝姚老鞠了一躬,对他说“谢谢”的时候,那一张母亲坐上去就觉得屁股热乎乎的椅子上早已坐了新的病人,姚老此时正凝神静气地在给病人号脉。
母亲侧面看过去,一派仙风道骨,气度非凡,犹如电影画面,永远定格在母亲的脑海里。
事后,母亲总结道,好郎中就是这样!江春华还说几句话,不过话也很少,姚老则根本不说话。两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这说明这两位医生对自己的医术都极度自信。病人是奔着想治好自己的病来的,一个医生,如果自信自己有本事能治好病人的病,他无须讨好、取悦病人!
接下来,又一次见证了中医的神奇。
就是这一副药,母亲服用以后,视力日渐好转,眼疾就这样好了。
到了我读小学的时候,母亲经常带我们去看电影。有时,去电影院买到的票,座位在十几二十排。我因为近视,觉得不戴眼镜有些观影模糊,而母亲好像全然不在乎。旁人怎会想到,这个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一度眼睛都快瞎了!
母亲的眼疾,大约在十年后有一些反复,她便又一次去找姚老看病。这个时候,姚老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一个叫做姚方未的中医坐在他父亲先前坐过的位子上继续接诊。
姚方未态度很是和善,听说母亲曾经吃了他父亲的药把眼疾治好了,便十分伤感,唏嘘了一番。他也给母亲认真号了脉,并且看了母亲的舌象,还认真询问了母亲一些有关疾病的问题。
最后开方的时候,母亲注意到他是用钢笔写的方子,而且字远没有他父亲写得清朗、挺拔和厚重。
母亲吃了这个方子的药,明显觉得效果比他父亲的方子差多了。
于是,母亲又找了去。
这一次,母亲把姚老的方子带上了。她满怀敬意地把方子给姚方未递上,无限敬佩地夸赞姚老这个方子的神奇。
姚方未此时少不了又开始沉浸在对父亲的怀念中。他认真地看着这个方子,然后,同样深怀敬畏地几乎原封不动地用钢笔把这个方子抄了一遍,交给母亲,让去抓药。
母亲注意到,他在抄方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他看了好一会儿。
是看不清父亲用毛笔写的字,还是他对父亲开的这味药有疑问,有异议?母亲不得而知。
母亲重新服用姚老的药,眼疾又一次稳定了。以后,她也不大老远地去找姚方未了,医院,随便找个中医大夫,就让他抄一下方子,好去抓药。
抄方子嘛,是个中医都会,何必再劳驾姚方未?去一次那么远,他还是专家,不但挂号难,挂号费还贵不少呢。母亲一定是这样想的。
2019年,医院看一位中医专家,想让他给我开几味调理胆囊息肉的中药。
这位年轻的专家无奈地摇着头说,没用的,开什么药都没用的。一般就是观察,等到它长到一定大,就做手术。
他正在跟我讲着,有人敲门,进来一位患者,把一个现在的方子递给他,请他抄一下方子。
这个方子刚刚抄好,又有一个患者进来,又把一个方子递给他,还是让他抄方子开药。
我看到这一幕,眼前立时想象出母亲带着方子让姚方未抄方子的情景。
想必缺乏医术的中医,大约也就是替人抄抄方子,开开药了。
不过,眼前的这位能够愿意抄方子开药,也证明这位医生有自知之明,值得为他占赞。
抄方子也是学习。姚老给我母亲开的方子里,第二位药是五味子。五味子有舒肝的作用。我母亲分明眼睛不好,姚老怎么给我母亲舒肝呢?
没错!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眼病的根源在肝,所以,姚老用了平肝、舒肝的一味药。
看看,何止抄方,连读方都可以学到一点杏林高手的治病方略。
可惜我只记得这个方子中的两味药,其它的一切都随医患二人的驾鹤归去,烟消云散。
(未完待续)
插图为金侬书法作品。
关于金侬:
本名张扬,书法落款名金侬,常用笔名废墨。
著名书法家,知名影评人、记者,资深媒体人,小说家,编剧。
中国文联编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丝绸之路电影节评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会员,中国书画院会员,中国书法名家联合会理事,中国民盟书画院会员,中国民盟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书画院会员,清华附中特聘专家级书法教师,文化部老年大学特聘书法教授,原《大众电影》杂志编辑总监。
更多资讯,可搜寻互动百科金侬词条,百度一下金侬书法,或可